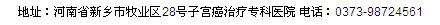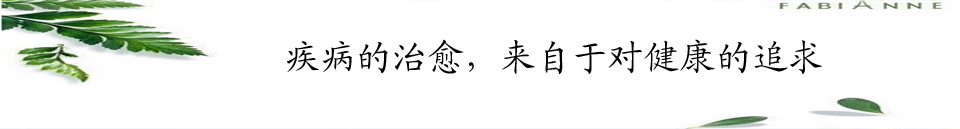
我52岁,为了自己的身体,做了一件对不起
你幸福吗?
1
医院出来的时候,觉得这辈子完了,我才五十二岁,怎么这种病就让我得上了?!
早上,我妻子王雪对我说:“老周啊,医院看看吧,老是这样呕吐也不是事啊?”
我笑笑,说:“这不算事,这几天老想吐一定是那天和李文喝酒,吃了不干净的路边摊。我的身体壮得很,你还不了解?”
王雪静静地看着我,有五秒钟,说:“医院看看得好!”
我笑笑,不以为意。等到上午王雪去单位了,我再次呕吐感袭来,我才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。我给同事李文说了一声,医院。
医院挂了消化科的普通号,可是当我对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大夫说了自己的症状后,她让我去血液科检查。我到了血液科少不了一番全面检查。当然,我也不奇怪,医院哪个不是这般操作。这就像小孩由爬开始学走路一样,已经成为了常态。但是,最后我去了肿瘤科,那个三十多岁姓胡的男大夫看着我的CT片,漠无表情的对我说:
“你好,你这个是胃癌,肿瘤已经很大了,请马上办理住院治疗。”
我一愣,我听清了胡大夫的话,可又觉得他说的不是我,我就是想吐,怎么能和胃癌沾边呢?医生也喜欢开玩笑吗?
胡大夫又说:“去吧,赶紧办理住院。”随后他在我的病历本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。
医院大门,我仍然很是茫然,我身体这么壮,怎么会得癌症?我想,一定是医生搞错了——是人,不都会出错吗?——所以我也就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了。
我开着两个月前买的新车,收音机里面放的是一首已故港台女星的名曲《甜蜜蜜》,公路上车不多,偶有零散的青年人,但都行色匆匆。
晚上王雪问我,“老周,医院了吗?”
我说“去了”,但没有告诉她医生对我的“误诊”,我只说:“我就是个肠炎,医生给我开了点消炎药。”
王雪“嗯”了一声,好像放下了心。但是那天晚上,我们关了灯,想要睡觉的时候,我的呕吐感再次袭来,并且这次开始时甚猛,我还没有走到厕所,就吐在了客厅的地板上,王雪趿拉着拖鞋,慌张的问我:“老周,你这是怎么了?”
我没有回答她,地板上是我晚上吃的面条,那股酸腥的恶臭,让我还想吐。可是我的胃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可吐了。
十分钟后,我弯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王雪一边清理我吐出的东西,一边问我:“老周,医院?你到底得了什么病?”
我还是告诉她我就是“肠炎”,但她不信。第二天上午,医院,我再次经过了繁琐的检查,得出了和昨天相同的结论:胃癌。
并且还是晚期。
2
王雪哭着说让我住院治疗。我笑着说:“先不住院,我手头还有老多事没处理,等办完了就来住院。”
王雪不依,在医院的大厅里扯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。我生气了,当这么多人拉拉扯扯,算什么事啊!
我打落她的手,转身往停车场走。王雪在身后紧跟着我。我们上车后,她说她来驾驶,我怒道,我还没死呢!她不说话了,坐在副驾驶上用手擦眼泪。
其实我能有什么事可做呢?
在单位里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,领导不好意思辞退我,不过是沾了我已故老父亲的光,碍于情面罢了。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做(其实有,我也做不来)。
在没有得病之前,我原计划,再干个两三年,办理个内退算了,也好把位置给年轻有能力的人腾出来,大家都高兴。不过我每月四千多块钱的收入,倒给我这个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明显“质”的变化。我如果内退了,工资和以前持平还行,要是比以前少了,我们这个家可怎么办啊!
我儿子周明二十五岁了,因为学历不高,只能给别人打工,过得也是朝不保夕。更为关键的是,她都二十五岁了,连带个女孩回家让我们见一面都没有过。
王雪也托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,可不是人家看不上他,就是他看不上人家。有几个他们两人谈对眼了,可女孩一听周明说起我们的家庭情况,女孩断然拒绝。我很觉得对不起儿子,我的无能不仅没能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,反倒连个媳妇让他也找不到。我常常为此深深自责。
但周明却并不以此为意,他对我说:“爸爸,你不要自责,婚姻这种事,不能以家庭左右的,我一准给你带个漂亮贤惠的儿媳妇回来!”
我笑笑;也许我也只能笑笑了。我拼搏了半辈子,得到的却是微乎其微。我一直觉得上天对我不公平,我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,而所得到的却是自己的一贫如洗,让人笑话!
而今我又得了要命的“癌症”,老天爷把我唯一的“资本”(健康的身体)也拿走了,我该怎么办啊!
我当然知道我该马上住院治疗,也许更应该马上接受要命的“化疗”,这样可能会让我多活几天。但是我要住了院,先不说花钱多少,我的家庭怎么办?
我经常笑着鼓励儿子、鼓舞妻子,要对未来充满希望。要是换成我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,鼓励、鼓舞他们,那将又是一番什么情景呢?
这万般罪恶的根源,不过是我没有“钱”,但这也将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我的烟消云散而泯灭。我的一生就像掉在河里不会游泳的“鱼”,在梦境与幻想中,慢慢沉默。
我开车到家后,对王雪说,我要去单位看看。
王雪很不放心地看着我,眼里的意思是,我哪都别去,在家里静养。但我怎么能听她的呢?我把汽车调了头,就驶向了公路。
其实我并不想去工作了几十年的单位,我本来就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。但我还是不自由主地去了单位,到了办公室,正好遇见新上任的马主任,他讥笑我说:
“老周啊,来上班了?”
我低着头不说话,很明显他知道我上午没来,意见很大。倒是同事李文赶忙过来给我打圆场,说我有事,上午请假了。马主任悻悻然离去。我给李文投来感激的目光。
李文和我儿子年龄差不多,按理说由于年龄的悬殊,我是不可能和他产生任何瓜葛的。可事情偏偏就这么怪,他一年前来到我们单位后,我俩人一见如故,就仿佛两条同类的虫儿遇到了似的。
李文喜欢下象棋,我也喜欢。所以闲暇时候,我们俩人经常抽着烟,下着棋。后来我们甚至一起出去吃饭喝酒,外人以为我们是父子,其实我们是一对真正的“忘年交”。
马主任走后,李文来到我身边,小声问我:“周叔,你是不是病了,身体不舒服啊?”
我笑了一声,说:“没有……”
但我话还没有说完,呕吐感就纠正了我的错误,它让我急跑向卫生间……
五分钟后,我看到了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李文,他脸上满是关切之色,但又仿佛知道我会呕吐似的。他递给我纸巾。
“周叔,这是我一个朋友,你去找找他吧,也许他能看好你的病。”
在办公室里,李文递给我一张泛黄、折痕严重的名片。
3
如果我不是把李文当儿子一样看待,我是绝对不会去见这个叫“崔卜”的怪人的。
这事很好理解,医院都给我下了“死亡通知书”,我不相信还能有谁能够改变这个“事实”。
我来的时候也曾想到了,这个叫“崔卜”的人一定是个“骗子”,不外乎给我开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草药,骗取我的钱财。
但我又想到,以李文的人品,他绝对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,又何况“死马当活马医”吧,我才下定决心来到了崔卜的家。
崔卜的家在城市的东北角,那是一片即将拆除的村庄,村民大部分都已搬迁走了,只留下崔卜一户,形单影只。因此我判断,他一定不是本地人,一定是个“过客”,以极廉的价格,租下了本地人废弃的房子,当做临时的落脚之地。
我的判断很快就得到了证实,崔卜就一个人,穿着件磨损很严重的蓝色冲锋衣。他皮肤微黑,一定是因为他长年旅行,风吹日晒的原因。他看上去和李文年岁差不多,只是他们两人的打扮,让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是“朋友”。
我在一张木凳上坐了下来,简明扼要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,其时我想他一定帮不了我的,也许他是个“心理师”,李文让我来找他,不过是让我减少对死亡的恐惧罢了。
他听完我的话后笑了笑,独自掏出一支烟点燃,猛吸了一口后对我说:“周叔,你的来意李文已经告诉我了,我明确地告诉你,我可以帮你!但是这世间的万物都是平衡的,你如果身体健康了,就会有另一个人承受你的痛苦。不知道你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?”
我冷笑一声,他说的是什么话呢,别人能代替我生病?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
显然崔卜看出了我的疑惑,他抽了口烟马上又说:“周叔,不是看在李文的面子,我是不会给你说这些话的。你既然不信,那么请便吧!”
他在逐客,其时我也想回去了。可是我那不争气的身体偏偏在此时让我想吐,因此我又在崔卜家停留了改变我命运的一个小时。
……
4
我回到家后都快晚上七点了,王雪关心地问我去哪了,怎么打电话不接?我说和“李文下棋”。
饭菜已做好,两荤一素,都是我爱吃的。我不想吃,但王雪劝我多少吃点,我吃了一碗面条。
王雪说周明打算开个汽车美容店,“现在他正和好朋友商量这事呢?”
我应了一声,想,他开汽车美容店一定会赔钱。
王雪又问我,要不要把我生病的事告诉周明。
我想了想说:“算了吧,过段时间再说吧!”
王雪又建议我明天住院,我随便敷衍了她一下。其余我们无话可谈,九点多钟就上床睡觉了。可奇怪的是,我那一夜居然没有了“呕吐”的感觉,我甚至还有一种“做爱”的冲动。当然我什么都没有做。那一夜我睡的很熟,反而是身边的王雪翻来覆去,一定是在担心我。
翌日清晨,周明看到我俩后吃惊的说:“爸爸,你今天气色真好!”
他顿了一下,又转向王雪,说:“妈妈,你的脸色可不太好?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呢?”
他笑了笑,开门走了。
我和王雪面面相觑,很显然她是过分担心我,才一晚上没有睡好的。
我们吃饭的时候,医院。我笑说,儿子都说我“气色”很好,今天就不去了,单位还有好多事呢。王雪拗不过我,吃完饭后,我们各自上班。
到单位后,李文笑着问我,感觉怎样?我说,没什么感觉。
“周叔,那就对了!你没有再想吐吧?这就说明你的病在慢慢变好,周叔,”李文停止笑容,“你一定要做到答应崔卜的事,否则你会受到百倍惩罚的,到那时候,谁也帮不了你了!”
我点头笑笑,心里想的却是,崔卜说的话是真的吗?
5
不过从那之后,我的身体真的渐渐好了。我从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稀奇古怪的东西,可是我的亲身经历,又让我不得不信。为此我只能履行对崔卜的诺言,我往他的一张卡号上转了五万块钱。
但这只是开始。
医院复查,当我做完了所有的检查,拿给那个姓胡的医生看时,他不耐烦的说:
“朋友啊,你一点病都没有,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做检查吗?”
我笑着走出诊室,很显然胡医生早已忘记了我是谁。
我小兄弟李文,也再不问我身体的事了。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,下象棋,不论聊得多开心,喝了多少白酒,又或者我有意将话头转向崔卜,他总是顾左右,而言他,就仿佛他从来不认识崔卜这个人。
好吧,李文不愿意说,我也就不问他了。他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但他不给我讲,我可以去找崔卜啊,我又不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
不过等我驱车到了和崔卜初此相见的地方,哪里已变成一片废墟,数辆拉建筑垃圾的货车穿梭其间,四周一片狼藉。
我明白崔卜已经走了,可是我不为没能见到他而觉得惋惜。我反而觉得我就不该再见他:我和他本就是两条路上的人,有什么共同语言呢!
此后我的生活、工作相当的顺利,先是我被局长提拔成为办公室主任——以前的马主任做了我的副手。紧接着我儿子周明的汽车美容店开业,一炮而红。周明也因此找到了漂亮可人的女朋友。我很高兴。
但我高兴归高兴,我从来没有忘记对崔卜的承诺,我给他打的钱,从最初的五万变成了十五万。可我从来没有心疼过。
万事皆平衡,我们家除了我们父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与此同时,我媳妇王雪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6
讲我媳妇王雪的改变前,先说说我俩的恋爱史。不然,你一定不会听懂这个故事的。
在二十六年前,经我爸爸的朋友介绍,我和马玲成了男女朋友。
马玲这个人性格开朗、活泼大方,我很喜欢她。同样,她也很喜欢我。
她爸爸和我爸爸是平级关系,我们两家人都没有意见,我和马玲在朝着众人期盼的方向发展。
但就是这时候,王雪出现在了我身边。他告诉我,马玲根本不爱我,只不过是在玩弄我而已。我当然不相信了。
二十多年前的男女,哪里有现在男女这么有心机,那个时候,爱就是爱,不爱就是不爱。他们不会和你扭扭捏捏的玩弄人。
更何况了,王雪只不过是我初中的同学,我和她早就不联系了,她冒冒失失的找到我,说我新交的女朋友在“欺骗我”,你说谁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!
我想,王雪不过是嫉妒马玲比她长得漂亮罢了。女人嫉妒起来,什么事都是做的出来的。
可是后来的发展却大出我的意料,我和马玲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,可有一天她告诉我,我们不合适,之后就决然和我分手。我对她万般解释,她连听都不听,就像我是只苍蝇一样,想法撵我走。
此后不出一年,马玲和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结了婚,让我彻底死了心。这时候王雪天天找我,我已经看淡了婚姻,又加之她的甜言蜜语,我就凑合着和她结了婚。
但是我父母都不喜欢王雪,他们说这女人太有心机,我早晚吃亏。父母是不会对我有恶意的。可我和王雪结婚后,她也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只不过等到我儿子周明五岁的时候,我偶然听说当初马玲离开我,是因为王雪从中挑拨。但此时木已成舟,说什么也都晚了。
不过我从那个时候起,开始恨起王雪。
这种恨是一种表面不显露的恨。
现在王雪的报应终于来了,在我去找崔卜四年后,有一天她对我说:“老周,我这两天胸口老疼,你说我是不是得病了?”
我说:“怎么会呢,一定是你吃的太辣,上火了。多喝点水就好了。”
王雪说“嗯”。
说实话,王雪第一次给我说这话的时候,我确实没有当回事。人嘛,谁没有个头疼脑热。
可是等到她第二次再给我说起,我就多了个心,医院看看。她疲惫不堪地说:“刚在单位体检,我一点事没有,不去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,脸色苍白的又说:“再说了老周,你的癌症都能自愈,更何况我这小病了!”
但她不是我,她的病像烟花一样蔓延全身,等到她医院,自然是癌症晚期了。她吓坏了,当即就办理了住院手续,接受化疗。
可是即便如此,也没能挽回她的性命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有气无力的拉着我的手问我:
“老周……你的,你的癌症是……是怎么好的?”
但我只是哭。
若干年后,我尝想起王雪临死前的那一幕,如果我告诉了她答案,不知道她会不会恨我?!
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,我拉着再婚妻子马玲的手,我感觉到的只是“幸福”。
是的,我觉得自己很“幸福”!